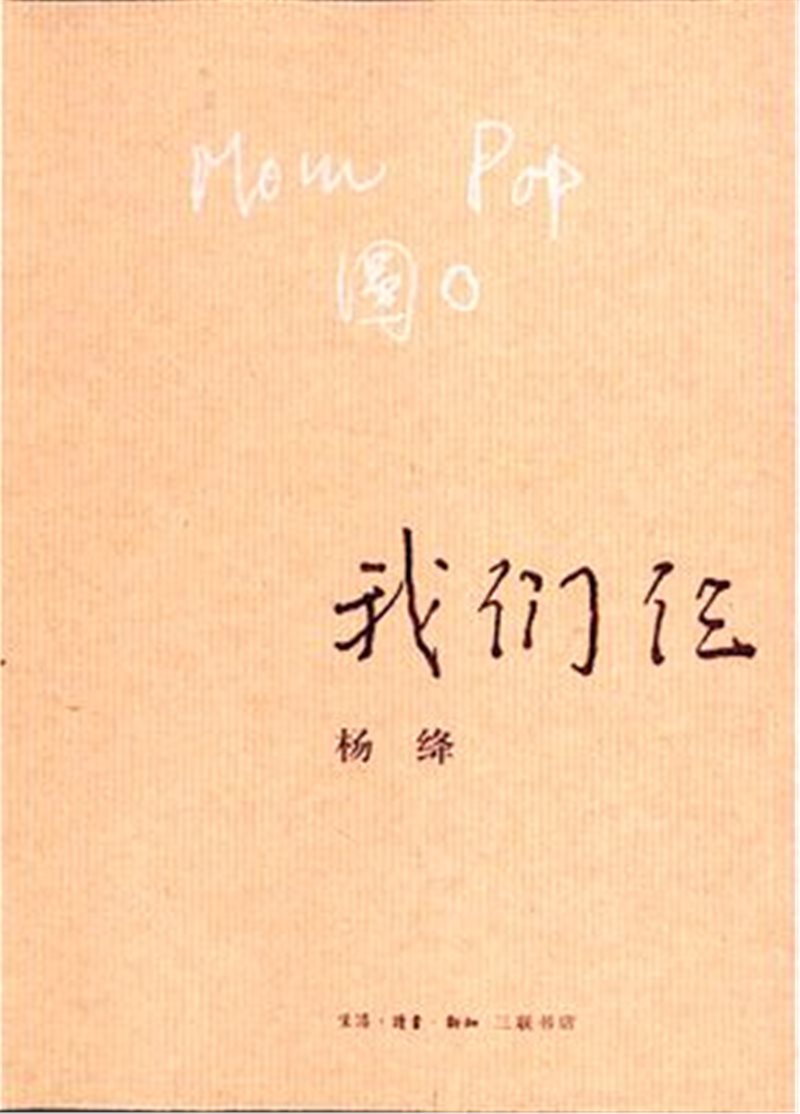痛并快乐着——读杨绛《我们仨》
《我们仨》是钱钟书夫人杨绛91岁高龄时撰写的关于丈夫和女儿的36年生活的回忆录。这本散文集分为三部分,分别是《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一二部的文字是痛苦的。第一部《我们俩老了》很简短,就一页。在两千来字里满是催人泪下的孤单、慌乱和凄凉:
忽然钟书不见了,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踪影。我喊他,没人应。只我一人,站在荒郊野地里,钟书不知道哪里去了。我大声呼叫,连名带姓地喊。喊声落在旷野里,好像给吞吃了似的,没留下一点依稀仿佛的音响。彻底的寂静,给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也加深了我的孤凄。往前看去,是一层深似一层的昏暗。我脚下是一条沙土路,旁边有林木,有潺潺流水,看不清楚溪流有多么宽广。向后看去,好像是连片的屋宇房舍,是有人烟的去处,但不见灯火,想必相离很远了。锺书自顾自先回家了吗?我也得回家呀。我正待寻觅归路,忽见一个老人拉着一辆空的黄包车,忙拦住他。他倒也停了车。可是我怎么也说不出要到哪里去,惶急中忽然醒了。
文字不长却无比的落寞惆怅,催人泪下。其中有伤感,有迷茫,更有追寻 … 这第一个梦里,“我”梦见钟书自顾撇我而去。于是醒来时便向他埋怨,钟书只是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于是钟书似乎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个长达万里的梦。
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 ,“万里长梦”把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揉进一个先欢喜后悲伤的生离死别的场景。她在文章中用悲伤的笔调写道:“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是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她是用“心被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她心上的痛和不舍。心是何等柔软的物体,哪里经得捅,还绽出血泡来?而血泡“像是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比喻说明她早已是流泪了。而当病中的女儿述说对娘的思念时,“我心上又绽出几个血泡,添了几只饱含热泪的眼睛”,母亲心上为孩子而生就的血泡是怎样的痛呢?不要说是死亡路上的折磨让她痛彻心骨,就是平时女儿一个小小的摔倒也是会让她心里禁不住受惊吓,当看护了半生的女儿最后抗争不过狰狞的死神终于永远离她而去时,“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这个世界上最让人悲痛的莫过于白发的父母为先去的黑发的儿女心里流出的浑浊的泪水,她说老人的眼睛已干了,只会心里流血。先是一个血泡,继而又是几个,最后是心里盖满了血泡,老人一颗的心变成全是血泡,痛苦可想而知。白发人送黑发人让人痛不欲生!“我的心已结成一个疙疙瘩瘩的硬块……每跳一跳,就牵扯着肚肠一起痛”。她的心里怎能不痛呢?女儿这么一个“强父母,胜祖宗”的“可造之才”却只能“上高中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怎能舒坦?“自从失去阿瑗,我内脏受伤,四肢乏力……(钟书)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
然而等不到在时间的流失里慢慢愈合伤口,仅仅一年后,她的爱人钱钟书,她的相守一生的爱人,也终于强睁着眼在说完“绛,好好里(即‘好好过’)”后,终于也离她而去了。一家三个人也只剩下她一个了,她说她愿意变成高山上的一块石头,守望着丈夫和女儿离去的背影。最爱的人也走了,家已经不再成其为家了,“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客栈总是不能久留的,总是要离开的,留下的也只有思念,可一个八九十岁老人的思念更让人触痛。先生书末有段“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的人生道路已经走到头了”看了让人心痛,一家人相聚只有在梦里或者那条与生路相反的路上。
杨绛先生将失去亲人心底的痛苦,以及死亡来临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却什么做不了的无助感,表达得无比真实,触人心弦,没有撕心裂肺,却平淡得令人唏嘘。于文学而言,死亡是最难以表达的主题,尤其是写死亡带给人的痛,稍有不慎,文字便会显得僵硬,哭声便会象干嚎,结果只会让人产生排斥。但是杨绛却写得令人动容,剜人心的情感在人心里来回流动。这是因为她对女儿和爱人的爱很深厚,深厚到未有文字前便已经占据了人的心灵,这种爱在经历近六十年的人生颠簸后显得越发珍贵,而一旦失去时,痛苦自然是成倍的,作者将痛苦的心情藏在每一个看似平和的文字里头,而一咬开却又是血淋淋的。
但书中也不全是悲伤,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里,杨绛先生用平淡而优美的笔调讲述一家人的一桩桩趣事。
幸福的一家要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我喜欢读图,附录二中女儿钱瑗画着父亲钱钟书没带假牙抿着嘴的样子,女儿在漫画上写着“衣冠端正,未带牙齿”,题目叫《赛丑》,活脱脱将钱先生的窘态细致刻画出来,着实可爱。两年不见钱钟书,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瑗瑗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幸福的一家要有一个单纯有趣爱妻子爱女儿的老爸——
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早起,钟书照常端上早饭,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这一次不是)钟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每天临睡前钟书都在阿瑗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去参加国宴。钟书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那人说:“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钟书则说:“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那人于是说:“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钟书很直接:“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于是一直没有出门。
幸福的一家要有一个朴素能干的老妈。杨绛先生不仅文笔了得,换灯泡,做家务,一样都没落下。
这幸福的一家人平等自足,在家里扮演各种的角色。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一起,相守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我常一个人在深夜读《我们仨》,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在于用生活的感受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愿“我们仨”都能不虚度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