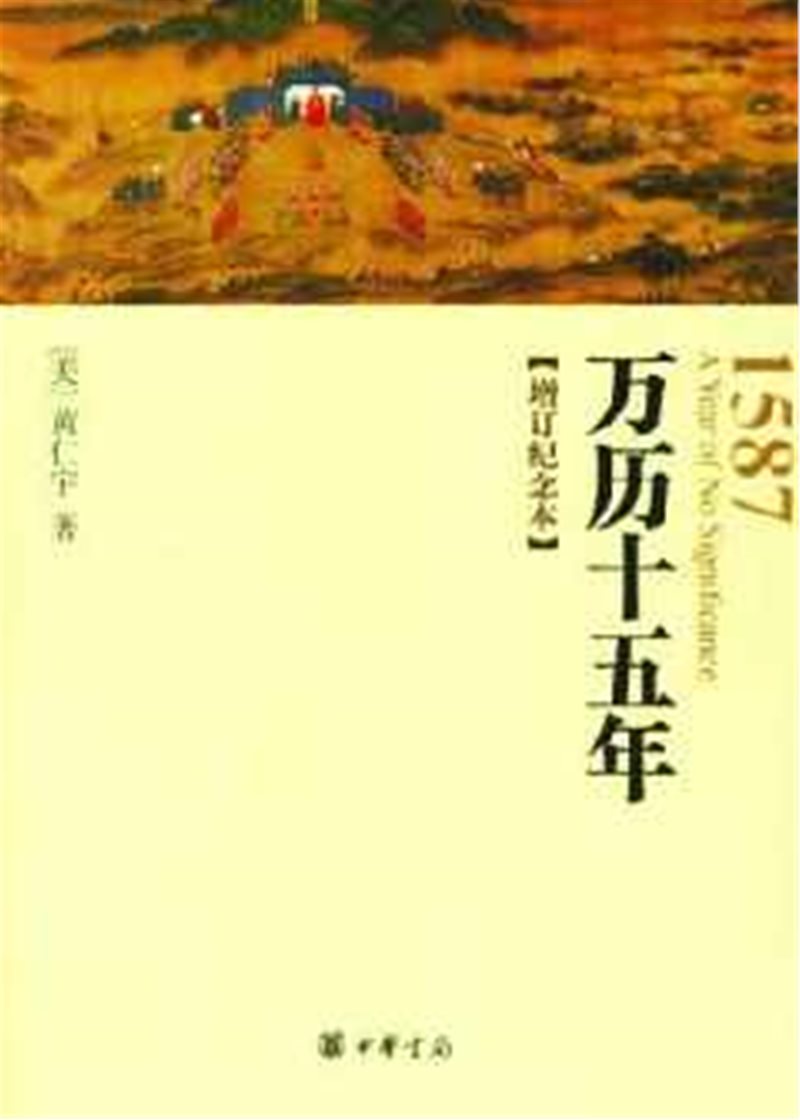从《万历十五年》看史学的功能
我初读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是八十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后经历周折有幸收藏一本该书82年中华书局第一版,闲暇时曾多次翻阅,虽感慨颇多却未形成文字,今年春节期间再次翻阅,作此小记。
《万历十五年》英文本在美国若干大学采用为教科书,还有法、德等译本,可见影响之大。在国内也多次再版,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请注意“非历史专业者”的界定,因为在历史学界,更多人不买他的账,甚至说黄仁宇“是历史学界的琼瑶””其作品“不伦不类”,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
这种现象正是我感慨的地方。我大学就读历史专业,深知历史研究之艰辛,有时为了求证一个观点,连续数天翻阅史料而一无所得,有时甚至要要到异地查阅资料。一位专业历史学者,穷其一生能写出真正有分量的、能公开出版的专著也就一两本,甚至只有发表论文数篇,这不能不说是其心血之结晶。而国内历史学界传统的风格,无论是一部著作或一篇论文,作者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往往长篇大论,引经据典,显示其有理有据,逻辑严谨,其引用的艰涩难懂的古汉语,特别是冗长的论证文风,使他们的心血只适合在一个很小的专业圈子内流通,把大量的非专业读者拒之门外。这就不得不使人思考,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或者说史学的功能是什么?综合我所掌握的史学理论知识,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其一,认知功能。是说通过对历史上的人和事的探究,获得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知识和经验,摒弃、警惕过时的,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观念。比如如何处理与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同事、朋友、领导的关系,如何处理与社会、国家的关系。
其二,借鉴功能。通过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探究,总结前人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经验教训,继承经验,汲取教训。比如我们今天提倡忠于国家、孝敬父母的观念就是对中国古代提倡的忠君孝亲观念的继承与发展。
其三,职业功能。也就是说,给一部分人提供了一个职业,以此为生。目前国内从专门研究机构到大中专院校,从中学到小学,从出版社到杂志社,有一个群体是以历史研究、教学、编辑、出版发行等为业的。
历史是人类已经逝去的过去,今天的人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将其复原,也无法将其再现。今天人们之所以研究它,主要意义,在于其认知功能和借鉴功能,像《万历十五年》一样,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出现的易中天、于丹热,说明大众需要了解历史、了解历史文化。如何用最通俗易懂,又有知识性和思想性文字把自己的研究呈献给大众,应该是历史学家价值的体现,否则就成了为研究而研究。史学界对黄仁宇先生的态度,反映了我国当前历史研究的现状,制约了史学功能的发挥,这是令人遗憾的。正像刘志琴在《黄仁宇现象》中说的:“在史学家们喋喋不休争议这算不算学术著作的时候,读者却作了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文化层次低的,是作家。如果对历史有兴趣的文化精英都不垂青国内的史学著作,那这些著作又给谁看?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万历十五年》的问世,与黄仁宇先生“半路出家”的丰富经历以及他的“大历史观”紧密相关。他不仅研究中国古代史,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仅研究中国历史,也研究世界历史。而国内历史学家们大多是“专业”出身的学者,是断代史方面的专家,与黄仁宇相比,认识历史问题的视角差别较大,往往就事论事,缺乏对历史的通识,这也是令人遗憾的。
当然,黄仁宇先生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认识也许有待商榷,但他研究历史的态度与表达自己见解的方法,我认为却是历史研究的必由之路。